 |
4月26日,《山河袈裟》作者李修文、著名导演宁浩、作家韩松落,3人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给读者做了一场有关文学和电影的分享会。
从《山河袈裟》说起,李修文谈到了自己多年的写作困境,以及人民与美给自己带来的写作上的奇迹般的“遭逢”、宁浩讲述了在《疯狂的石头》拍摄期间窘迫的生活,以及自己对影视创作的理解,李修文说:写作,就是我披在身上的袈裟,宁浩说,找到创作的道路,首先就是忠于自我。
人民与美、文学与影视、故土与乡愁,李修文与宁浩的分享,引发了一场有关人生与困境的思考……
宁浩:《山河袈裟》挖掘出了人性最脆弱最本质的东西
宁浩:我和修文认识很多年了,在一个觥筹交错的夜晚,我们俩一边聊天,一边喝酒,那种一见如故的感受很强烈。
我们老家有一句话“与临不睦、劝邻修屋”,说的是,如果你与邻居不好就劝人装修,然后他们家肯定会打架,打起来就会散。为什么修屋就会打架呢?其实是说,审美这件事是非常难以沟通。
但我跟修文更多的沟通是在审美层面,我觉得我们俩很多见解都一致,包括对艺术、电影或文学的创作观和美学观,甚至对时代的关注,都很一致。这很难得,所以我们俩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李修文:那是我们的初识。
最近我们又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到祖国山河大地去看树。大概两三年前,宁浩导演对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尽管爱莫能助,但我目睹了宁浩很多次艰难的创作过程。一个外人可能对喜剧导演充满了狭隘的认知,并不清楚一个喜剧导演灵魂深处的痛苦、虚弱。我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肯定是首先承认自己的生命力乃至创造力虚弱的部分,才可能洞穿虚弱。我不光看见了宁导真实的虚弱,也看见了他对于虚弱真实的抵抗,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而且可以在很多的时刻,对自己产生某种巨大的鼓舞。
宁浩:修文的书我在读的,因为他有审美洁癖,有很坚定的价值观,这样的作者非常少。
修文的散文集,说是散文,在我看来也像小说,他加了很多的情境,那些情境,对我来说都是深入人心,我读完以后,觉得看的不是文字,都是画面,非常有人物感、电影感、视觉感,这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对于创作的认识,对于从狼狈不堪的生活里面去挖掘人性最脆弱、最本质的东西,对于整个世界的关怀和关爱,这都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所以《山河袈裟》,他的小说和散文,我都非常喜欢。
李修文:这么多年,我在宁浩身上,首先是看见了他作为一个创作者矢志不渝的对于自身的每一次遭遇的克服。
我理解的宁浩,可能跟很多人眼中的宁浩不太一样,我觉得他是一个嬉笑着秉持鲁迅传统的人。我们看他的作品,实际上,是深植了鲁迅先生的精神,回观自身、挖掘自身,他独特的气质赋予了对故事最诚实的认知。
可是这样一条道路无比艰难,因为这是在相当高的标准之上,我们私下里很多次交流过这个问题,他是既见人心又见责任,留给一般大众的是,他深入逼真地描绘我们时代的嘴脸,可是他的故事还有一些没有拍出来,是他讲给我听的,我从他的自嘲中见到了时代的人心。
一个导演,或者说一个创作者,身处在他自己的时代里头,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发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生活的风貌。我们很难从今天的电影里头看到这种风貌。几十年后,如果有人来回望今天这个时代,宁浩的努力,他所描绘的这个人物、这个世界,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
关于创作:首先是真诚地面对自己
韩松落:不少的朋友都对创作感兴趣,大家在创作中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一开始我们站在可能性的汪洋大海里,这也能写、那也能写,玄幻、奇幻都能写,但当你真正的执行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能写,有些东西甚至不必去写,也不愿意去写。
我很想知道,两位是怎么找到自己真正的道路?
李修文:我觉得还是生活本身,因为我生活状态非常不好,每隔几年都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我从20几岁真正迈入写作这个行列以后,这个问题就严重的困扰我,20多岁的时候可以依靠审美、幻境和对于世界的想象,来进行创作,一个作家的起点很可能是从想象力开始的。
但是,你描写一件千年前的事情,也需要从当代生活里,获得可靠的情感源泉,否则很难描述。
我20多岁写了两部小说后,就陷入了非常长久的沉默期,对自己的创作的力,发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并且这种自我怀疑上升到,连一个适合自己的字词都找不到。
我很喜欢有一个大诗人叫德里克•沃尔科特,他说“要改变我们的语言,首先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诚实的承认自己的失败,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种失败当中,不要让躲在一个创作者的囚笼里无法自拔,让自己勇往直前,重新把自己还原成一个真正生活意义的人,以此获得这个时代新的激情。
一个创作者,有的时候会肯定这个世界,往往还有很多时候会冒犯这个世界或时代。
我曾一度承认自己很有可能终生再也写不出来东西了,并且我做过这种准备。
后来我觉得谋生也重要,今天的时代不太研究创作者的谋生问题,而今天的时代,谋生恰恰是最敏感的,就是一个人完成自己、执行自己,最终完成自己人格的最本质的通道和路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忘掉自己作为创作者的认知。我反而重新获得了和大众、世界重新沟通和契合的能力。
我觉得今天的时代无论你做什么,你只要从事创作,捍卫你的创作观、捍卫你的生活方式,是无比重要的事情。
我自己经历了漫长的暗无天日的一个时间段之后,我就真的不再把自己当做一个创作者,而把自己当做一个生活意义上的人,反而产生了奇迹般的遭逢。
第一个我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想象力对于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当你在这样一个最凡俗的日常生活,遇到了如此多的同路人,而同路人又给你提供了某种安全感,他们赋予你日常生活从来没有发现过的神迹般的意义。
我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我面临某件具体的物事:一个朋友、一场雪、一道闪电,我会产生某种具有宗教感般的感受,我就对身边的人或事物产生了某种膜拜之感。
我解决了“写什么”。
第二,“怎么写”。
过去我也写过所谓的先锋小说,也写过某种中国传统古典话本影响下的小说,到后来我开始改变自己的写作态度,我假设我不再有读者了,也不当做自己有对象,我要怎么写?
我想,我就像写日记一样,就像求神拜佛一样,我要诚实。如果你在佛前都不诚实,可能佛也救不了你,所以态度上我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很奇怪,当态度重大转变后,词汇、语言风格,那些过去连碰都不会碰的词,会自动浮出水面,生活已经帮你验证了你信赖的字词,你甚至可以窥见你的命运,写作就真正的和命运结合在一起,这是在写作非常困难的时期的深刻体验。
宁浩:我的感觉就是忠于自我。修文也说了,忠到什么程度呢?他举个例子求神拜佛,你得特别坦诚的面对你自己的一切,不管龌龊、崇高、渺小你都得接纳,你才有可能找到创作本质的一部分。
我刚刚在想,修文刚刚说我像鲁迅,我吓着了,我觉得我像阿Q,但是在剧中人里,你必须得进入到那个人物里头,并且你找到他与你之前的联系,我觉得特别重要,秉持人物创作,一定要进入到人物。
我并不是特别擅长写女性题材,我不是非常了解,我是一定要写我个人最了解的那个部份。我特别有阿Q精神,我也特别认同我是那样的人,那我就站在这种角度去写世界,这里头没有什么崇高和龌龊的区别,没有,但是你必须得特别真实的面对自己,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另外面对你自己的生活,就是你也不用到处去想,去哪挖什么东西,或者找一个多奇幻、多奇特的故事,就像修文说的。尊重身边的一切神迹,你身边的东西本身就是神迹,包括在座所有的同学,我也是北师大的,你们什么都可以写,你只要足够尊重你身边发生的一切故事,包括家长礼短,你同学、你老师、你自己,每一个都是一个故事,你可以写他们的内在,写他们的外在。
《山河袈裟》:回到人民回到美
韩松落:修文在2000年前后就凭借长篇小说出名,《捆绑上天堂》和《滴泪痣》,都以爱情为主题,都是城市背景。《山河袈裟》里有爱,但是没有爱情,背景也从城市转为更为广阔的天地,而且这本书不仅仅是写年轻人,有的是形形色色各种年龄阶段的底层人,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中间的多少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你写作的对象发生了这么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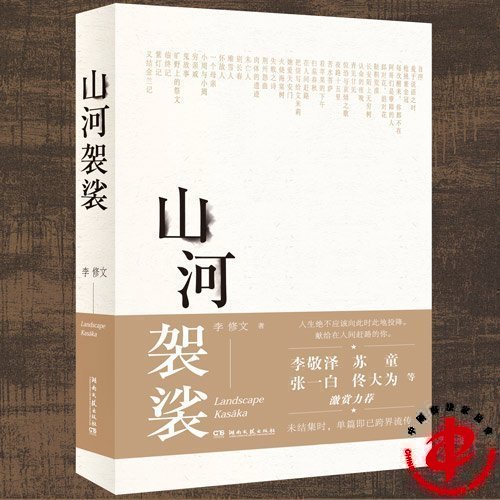 |
李修文: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我兴趣不大,不过,在《捆绑上天堂》和《滴泪痣》那两部小说中,我看起来是写爱情,实际上我对一个主题非常感兴趣,叫“生命力”。尤其我是一个生长在湖北,在深厚的楚文化影响下的地域,有个问题我一直很着迷,为什么屈原不继续宫斗而自沉于江水?这种赌气般的行为、过家家一般的斗争,让我一直很好奇。
我是通过爱情这个架构,探讨的是人的生命力。
所谓爱情,爱意的诞生、消亡或者萌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生命力的最大的体现,还有什么比通过爱这件方式来证明自己的生命力,更加有说服力呢?
其实创作、创造的过程,都可以表现人的生命力。
说到《山河袈裟》,我觉得还是生活本身带领我找到了我想踏足和描写的疆域,生活带领我见证了生活它里面一场场的奇迹,我也不认为我在写某种意义上的底层,大家都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底层,今天的时代你过得好也不高兴,过得不好也不高兴,我觉得我宁愿说这本书里头写了各种各样陷落在各自困境里的人,无法自拔也好,就此沉沦也好,站起来也好,所有的对于虚弱的抵抗和最终的穿透,实际上都是一个侥幸,就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听父母讲“这是命啊”。如我刚才所说,听上去好像是鸡汤,可是活到这个岁数,碰到这么多人,其实 “这是命啊”这句话,代表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外部的最清晰的认知。
我在写作上没有明心的野心或者策略,就是生活本身带领我走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我的语言发生了变化,我描述的对象也发生变化,那是我在某种黑暗或泥潭里头,碰到的一种从天而降的奇遇,把我塑造成了我过去无法想象的要成为的那个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命”,不是我故意的选择。
韩松落:修文还把一个词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他在《山河袈裟》里提出来的“反抗”,在这本书里面有一大段来讲“反抗”。他还提到过两个词叫“人民和美”,就是这本书的主题,但是我看了一下,他所讲述的人民和其他作家讲述的人民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人民对你意味着什么?
李修文:人民就是意味着同路人嘛,就是同伴嘛。我心目中的人民,实际上和所有的地方所认知的人民没有本质的区别,我觉得这个词可能在历经每一个阶段后,会填充进不同的内容,但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人和更多的人、人心和更多的人心。
也许有人觉得“众生”类似于这个的词汇,但我感觉“众生”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而人民是让个体感觉身在一个巨大的群体当中,让人产生依靠感,强烈的认同感,人民有一种情感的皈依所在。
所谓人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人民性。人民性意味着什么?历朝历代总是离不开集体、吾道不孤,人民性就是指“有同一种主张或者有同一种认知”。我获得了强大的依靠感,这是我不断的会使用“人民”这个词的原因。
宁浩:我对“人民”的理解,我刚才一直在想,修文说的那几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共性?修文用了一个词叫“遭遇”。
我理解,其实每一个人都是逆境,说白一点,人生走到后面发现无一不处在逆境当中,没有人不在与整个逆境做斗争,无论你是要活下去还是你要有点想法、你要获得幸福生活,你没有权利顺流而下,譬如社会告诉你,你得买房子,如果每个人都被迫去买房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知道为房子车子去奋斗,是一件很虚无的事情,自己是是被迫的。但大多数人仍然这样去做,甚至拼命挣扎地做。
其实不光人生是这样的,如果研究物理学,你发现都是一样的,所有事物,整个宇宙都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以一种破坏的、突破阻力的方式在行进。只要你行进,都有特别大的阻力,那个就是逆境,那个就是遭遇,是所有人民命运的共性的最大基础,它必然会提炼出某些类似我们感觉到共鸣的地方。
就像我们说我们要看作品,找到一个共鸣,我前两天跟人聊,什么样的人能做作家,我觉得都是那些小时候有沟通障碍的,或者边缘化、没有朋友,或者朋友比较少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从小极其渴望沟通,特别渴望找到一个朋友。
什么是友情,什么是爱情?我认为它们是一个东西,说白了,同性之间叫友情,异性之间叫爱情。
我们一般说找同类,爱情和友情都是找同类的结果,这个同类就是一男一女一见面,这女的长得我喜欢的样,男的也是我喜欢的样,那不是爱情,那是互为猎物,互相觉得对方是猎物,很难持续长久,它是个并肩关系。
但当家大家一块说那老师他傻,你也觉得他傻,那导演拍电影特别次,你也觉得特别次,这是共鸣,当两个人找到共鸣的时候,彼此会发现,不孤独了,就产生一种沟通。
我们穷极一生在寻找爱情、友情,都是为了避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所以其实我们不停的去搞创作,就像孤僻的小孩儿都适合搞创作,你可以用一个作品,获取最大范围的一个沟通的渠道,你跟大家产生了共鸣,这就是为什么创作人能够呕心沥血,一生都在追求和表达,还是要找到有共鸣的人,这是我对人民的理解。
韩松落:怎样看待“人民”和“故乡”?
李修文:我觉得人民可能还是那个人民,故乡可能就不再是那个故乡了。我们今天谈不上真正意义的故乡了,所有人的故乡都已经遭到了极大程度的篡改,这个故事里的很多当时者的命运,就在这种被篡改的命运里,展开了自己更加无法支配的人生,这本身也是我和他们,一起觉得很伤感和叹息的地方。
那至于人民,究竟还是不是那个人民,可能也不是,可能是我们过去在人民这个词汇的定义之下,对于过去时代的人民的认知,相对狭隘,一直以来我们的人民,就没有完全生活在一个桃花源般的语境当中,我们的人民从古到今,其实一直深陷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境里头。那么许多时候我们所认知的人民好像是载歌载舞的,是欢乐的,是像母体一样可以迎接任何的伤口,重新修复的长生所在。
我并不认为,我重新发现了我眼中的人民,我想我也没有特别的去赞美或者说是教训这一些人民,因为你必须承认他一直在,可是这涉及到一个作家的眼光或者说审美,或者说他的价值观的问题,你到底是要拿它开玩笑还是说不能开玩笑?
那在我目前这个阶段,或者说在写《山河袈裟》这本书的阶段,我觉得我还在滴血认亲,还在和大家走同一条路,喝同一杯酒,陌生人给我递上这一杯酒的时候,在我不足以为外人道的苦楚的时候,陌生人丢下一盏灯火的时候,我选择去发现、赞美。
韩松落:也想问宁导同样的问题,你上次回家乡是什么时候?
宁浩:得有两年了吧。
韩松落:那回家乡有什么样的感觉?
宁浩:不认识,已经不认识路了,连接点已经很少了,当时我记得我带了我们同事回去,到那个地方,我本来可以带带路,最后还得拿手机导航,我遭到了耻笑。我觉得确实是变化太大,还蛮震撼的,把迪厅的灯都搬马路上来了,五星酒店里都是光着膀子,我觉得挺有意思。




